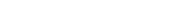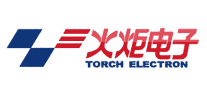除表彰私人捐赠,以往官方大型博物馆很少出现诸如“吴湖帆收藏”、“虚斋收藏”……乃至“石渠宝笈”等体现收藏主体的专题展。是时的展览,大多围绕着艺术家承前启后构成的艺术史展开。也许由于二十余年艺术品市场的高速发展,民间收藏之风大盛,特别是大陆新一代收藏家重新涌现,令已淡出人们视线四十余年的收藏家观念再度觉醒,收藏专题而非仅仅是艺术作品,已渐在官方博物馆近年的大展中,成为一个热门主题。
事实上,艺术史非但是体现着艺术家,同样也是体现着收藏家的趣味、意志与观念的一部历史。比如,若非明代由吴门画家导引的收藏之风的兴起,作为吴门绘画远祖的元四家其实是不可能得到后人追认的,更别提由此引发的重大的艺术史变迁——“吴浙之争”或者说“宋元之争”。黄公望是位行脚四方的道士,吴镇一度被认为是算命先生,倪瓒虽有贽财,但晚年却形单影只地以一叶扁舟漂泊于太湖浩渺的烟波中……若没有其徒子徒孙辈的杜琼、刘珏、沈孟渊、沈周乃至文徵明的继承,没有围绕着文徵明祖孙包括沈周等人的吴地收藏家们的一力追捧,这些胜朝时在江南文人小圈子里负有盛名,而于社会层面却默默无闻的高士或者说是方士,其作品安能获得“江东人家以有无为清浊”(沈周题倪云林画中所述)的无上荣耀?
惟其如此,以吴为核心的江南文人画审美才在苏州经济飞速发展的前提下,于明中期逐渐压倒了原先受官方扶持、秉承南宋院体的浙派风尚。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吴浙之争”、“宋元之争”,说白了其实正是以文人审美为核心的江南民间收藏,力压以宫廷审美为核心的官方收藏这一过程的一体两面。收藏对艺术史影响的实例,实际上不可胜数,只是过去对此缺少足够的认识。本文无意于此多费周章,而是要借“石渠”大展的机会略介绍以乾隆帝为首的清宫收藏的价值及其对艺术史嬗递产生的重要意义。
北京故宫举办的“石渠宝笈”特展,可视作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书画收藏展。“石渠宝笈”收藏,原本就是这座集中古政治、历史、文化、艺术于一身的伟大建筑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妨视为今天的所谓“软装”),只是由于过去意识形态的强调,对封建帝王意识的批判,对之不曾正视而已。故宫以“石渠”特展为其九十周年华诞庆生,因也最是恰如其分。
相对民间赫赫有名的张伯驹、庞元济、吴湖帆等收藏家,创建了“石渠宝笈”系列的收藏家——盛清时的乾隆皇帝,实在太过特殊。
清宫是自宋以后中国最大、最重要的艺术品与文物收藏者,尤以乾隆帝贡献为巨。
“石渠”典出《汉书》,西汉皇家藏书称“石渠阁”。皇家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历来属于“图书”也即“典籍”范畴。古代典籍曾是手书,后虽可以印制,但先贤手书自属典籍;绘画既包括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图,又有很多出于历代贤者贵胄之手,更曾作为重大政治事件与人物活动的图像资料(有类今天的影像),如《历代帝王图》《步辇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等,故书画在古代收藏领域,是仅次于权力象征的礼器玺印之外的国之重宝。
《石渠宝笈》经乾隆九年、五十八年前后两次编撰,分别称为“初编”、“二编”,嘉庆二十一年再次扩编,称“三编”。编辑人员众多,如张照、梁诗正、董诰、彭元瑞、阮元等官员,多饱学之士并善画之人,与皇帝一同对作品品评审定,并编纂成书。其工作量极其浩繁,堪称是书画领域足与编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相颉颃的浩大工程。此次特展,办展方特设“编纂编”,对《石渠宝笈》的编纂情况乃至在紫禁城与圆明园的书画存放地点详加说明,用心可谓精细入微。
乾隆帝在编辑《石渠宝笈》初编时曾下谕云:“三朝御笔,藏之金匮者,焜煌典重,……所当敬为什袭,贻我后人。又内府所储历代书画,积至万有余种。……应一并分类诠次,用志岁月。至臣工先后经进书画,……有可观览,选择排比,亦足标艺林之雅。”可见“石渠”收藏的范围首先是清代帝王手迹,其次才是古今书画。
历代帝王御笔,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相当的艺术价值。经过二十世纪的民主革命,特别是经“极左”时代对封建帝王将相意识的批判,有人对帝王手迹不屑一顾,而在收藏领域,御笔历来是热门且价值很高的品种。对此现象,如果放平心态去分析,并不难理解:既然孙中山、蒋介石、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重要政治家、学者,乃至汪精卫等历史人物的手迹是见证一个时代的重要文献,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那么作为古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家,特别是清代三位大有为之君的御笔,在一定的艺术价值之外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显然顺理成章。
除去作为重要文献的历代帝王御笔,“石渠”收藏才称历代书画。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清宫,御笔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历经数百年沧桑,书画的文化价值得以充分显现。今天北京故宫举办“石渠”特展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关注,但若仅仅举办清代帝王御笔展,虽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其影响可能就要小很多。权力与艺术准确地体现其价值,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唐伯虎在桃花庵里疯疯癫癫的唱辞——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是对此很好的诠释。
言归正传,在书画收藏上,由乾隆主导的清宫收藏堪称迄今为止的集古今大成者,这是无须争议的事实。虽然艺术水准与其前辈宋徽宗相比尚有不小距离,但乾隆帝毕竟属那个时代标准的有为“文艺青年”,其祖康熙、父雍正亦雅好文艺,惟康雍两代皇帝专心于开疆裂土、发展经济,至清代趋于极盛期的乾隆,始有闲暇与条件发展其文艺爱好。
作为其时天下一人的乾隆,虽有着一般帝王共有的骄矜之气,但却凭借其对艺文所特有的热好,构建起了清宫文物收藏的庞大体系,包括“石渠宝笈”书画在内的清宫文物收藏,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称迈绝前代,开创了北宋以还皇家收藏的又一鼎盛期。
当年的清宫收藏究竟牛到何种程度?简单直白地说,其主体,正是今天台北故宫所宝有的数十万件文物珍品,其中书画更是几乎囊括了唐五代北宋的传世名作。当然台北故宫高古作品的数量虽大(仅宋代作品即有近千件,相对而言,北京故宫质量较精,但数量仅其一半有余,而且作品尺幅也较小),但有不少在断代上仍存争议(台北故宫保留了清宫品评的旧说),然要不失为上古时期的扛鼎力作。而其在大陆的遗存,主要是清民易祚之时散出宫去,绝大多数为末代皇帝溥仪所盗、售者(这些珍品因长期存于东北,俗称“东北货”,其散佚过程可参见杨仁恺先生所著《国宝沉浮录》),构成了如今北京故宫、辽宁博物馆馆藏高古书画的主体部分。
如今为北京故宫收藏的“石渠”书画,主要是在溥仪逃离伪满州国时为苏联红军截获后由东北调拨北京,再有是在建国后逐渐寻访收集所得(除“东北货”外还包括在清末为八国联军劫掠之回流者,此次故宫特于武英侧殿陈列这类作品,如隋人《出师颂》、传展子虔《游春图》、唐韩滉《五牛图》等)。因当年是被盗出宫去,故大陆所存“石渠”书画大都为手卷、册页等易携带者,这也是何以台北故宫“石渠”书画特多大轴中堂的原因。溥仪盗出“石渠”名画,曾存于天津租界,后移至长春伪皇宫后的小白楼。比如现藏北京故宫,此次“石渠”特展中大名鼎鼎的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是当年为苏军截获者,后经辽博专家杨仁恺发现。而今辽博重器如唐周昉《簪花仕女图》、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宋徽宗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等,也尽皆小白楼中的“石渠”故物。辽博所藏所以能与北京、上海这民国时两大古书画集散地的博物馆分庭抗礼,所恃正是这批当年的“东北货”。
除此之外,经溥仪盗卖散佚的“石渠”书画,除今天为美日等国公私收藏外,仍有三百余件散于民间。由于“石渠”书画的显赫声名,这些作品一经面世,即便作者名头不大,往往能在市场上创出数千万元的天价,是即“石渠”品牌的魔力。可能有人对此不解,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今天台北故宫、北京故宫若有藏品散入市场,因其品牌的附加值,价格自会远胜同类作品。这亦如同著名藏家的专题,如老舍藏白石、梅云堂藏大千,价格远超品质相类的作品,实为市场的一般规律。
古书画作为记录国之兴衰的典籍,加之“石渠”书画在历代皇家收藏中的地位及其本身具有的重要艺术史地位,决定了此次北京故宫建院周年大庆倾力展出这批作品,必然成为轰动社会的盛事。
除了《清明上河图》,此次“石渠”特展的二百余件名作中,包括赫赫有名的书法——唐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即神龙本《兰亭》。相传王羲之真本被唐太宗带入了昭陵,神龙本历来被视作是《兰亭》最佳的唐代摹本,出版物上鼎鼎大名的《兰亭序》其实也正是这卷神龙本。乾隆“三希堂”法帖(“三希”者,一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一为王献之《中秋帖》,此二帖都被疑为摹本)之一的《伯远帖》,亦此次展览中的无价之宝,是比较公认的晋人真笔。而如前述隋人《出师颂》及宋徽宗、米芾、赵孟頫、鲜于枢等历代大家的法书,尽皆为学人顶礼膜拜的珍品……
至于绘画,则有宋摹《顾恺之<列女图>》《洛神赋》,忠实地记录了晋代高古人物画的格调风韵;传为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乃是山水画草创时代水墨与丹青并举的古老遗踪;《五牛图》传为唐代名相韩滉的杰作,此画仅明代项圣谟与近代吴湖帆的两件摹本,在近三年的两次拍卖中分别创造了近二千万元的天价。传五代黄荃的《写生珍禽图》,是其付子居宝学画的范本,从中可见出五代花鸟画已然达到的高度。宋徽宗《听琴图》《雪江归棹图》,皆这位传奇的不及格皇帝的署名之作,《听琴》应为代笔,《雪江》则历来被认为是亲笔,从中可以想见这位热爱绘画甚于江山的伟大艺术家当年的绝代风华。其他画如周文矩《文会图》、张先《十咏图》、赵孟頫《人骑图》、赵雍《挟弹游骑》、倪瓒《幽涧寒松》等等,无不为中国画史上百代标程的里程碑式杰作……
虽然“石渠”收藏地位显赫无比,但亦不无瑕疵。这主要是因乾隆帝好大喜功,非但“石渠”书画中杂入过一定数量的赝品(清代大收藏家高士奇就蒙他吃药),并且如著名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还曾因其个人好尚而被搞混真伪,闹出笑话。再者便是这位“十全老人”好品题,多钤印,令传世珍品被指有佛头着粪之嫌,因曾为民国时知识界诟病,尖刻者甚至有将“石渠”品牌斥作“帝王崇拜”者。这虽不无道理,但若细审其中原因,除却王权权威,不难发现很多作品前代已然误认,更兼资料匮乏,不比如今科技发达、信息通畅,易于比对(如敦煌壁画的发现),才是导致上述误判更为重要的原因。事实上,书画史上的一些基本风格,早在董其昌时代已然混淆(董氏水平虽高,但鉴定风格相比乾隆更为随心所欲,凭空臆断者甚多)。况且虽有缺陷,但这却与“石渠”书画在历代收藏家中深入人心的神圣性,形成了有趣的反差。在笔者看来,这正有如今天国外的某些人士,从政治观念出发将鉴定亦视作服务贵族的“等级主义”行为,是一对长期存在而无法消除的矛盾。
今年是故宫建院九十周年,“石渠宝笈”特展乃是此次故宫大庆最值得关注的展览。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九十年前的故宫建院之初甚至更远的时日,“石渠”书画展出时,已然引起过社会与艺术界空前的反响。
因末代皇帝溥仪居宫中窃运文物、珍宝,引起各界愤慨,蔡元培等呼吁政府干涉并学习西方建立博物馆制度,将宫中文物公开展示。当时供职于内务部的江南画家金城即向部长朱启钤提出成立古物陈列所的建议。经北洋政府批准,金城被任命监修工程,仿照欧洲博物馆制定了陈列规划。1914年1月,中国第一个国家博物馆的雏形——内务部古物陈列所成立,在紫禁城武英殿与文华殿展出了清廷原先置于热河(承德)与奉天行宫(今沈阳故宫)中的大批文物。九十年前的1925年10月10日,在古物陈列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再次展出了秘藏千年的奇珍名画,引起巨大轰动。大批观众纷至沓来,拥挤至不能转侧。百年前之公开展示这些艺术珍品,迅速在书画创作与鉴定领域引发了重大变革。
乾隆帝开始编纂《石渠宝笈》时,内府规模空前的搜求令民间收藏臻于前所未有的匮乏境地。珍宝一旦入宫再难见天日。惟其如此,宗法宋元的清初四王特别是画通南北两宗的“画圣”王石谷,成了全社会画家学习的楷模。这无非是因古画无从得见,学人希望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了解中国画古老深厚的传统。然而,这却导致了“家家大痴,人人一峰”的学元画、实际是学画四王的“格式化”局面,并持续近三百年。审美长期的单一化与固定化,终引发了清中后期直至近代声势浩大的反“四王”艺术革命。
封建制度的终结,上古名画的重现人间,现代博物馆及出版展览事业的兴起,终于全面引爆了近代书画界的这场变革。其始作俑者,正是率先得见“石渠”名作的金城,他非但自己力学,更提出了以唐五代两宋画风力矫明清文人画流弊的画学主张。在雅好书画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支持下,金城在北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画学研究会,聚集起周肇祥、陈师曾、于非厂、胡佩衡、吴镜汀(启功的业师)、秦仲文、陈少梅、惠孝同(此公富古画收藏)等一大批以古开新的名家,北京画坛局面为之一新。而随着“石渠”名画的面世与影响,至1930年代,南方以张大千、吴湖帆,包括稍晚一些的谢稚柳、陆俨少等为代表,亦开启了师古开新的艺术新潮。
“石渠”书画的重见天日,非但引发了创作的革新局面,更极大地推动了古书画鉴定的发展。尤其是谢稚柳、徐邦达、启功、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等这些新中国博物馆系统的泰斗级人物,得益清廷崩溃的机缘饱览“石渠”故物,在综合各类资料的基础上,与张葱玉、韩慎先、溥儒、张大千、吴湖帆等前赴后继,通过广泛而科学的比对研究,厘清了上古画史嬗递的诸多关健问题,取得了“后‘石渠’”时代古书画鉴定的一次重大飞跃,奠定了如今中国书画鉴定的基本格局及观念与方法。“石渠”收藏的一些缺陷,包括乾隆以前的误判,其实也正是通过这些站在“石渠”肩上的大家的努力,逐渐得以矫正。
这里再从另一角度介绍一下“石渠”的收藏趣味及其对艺术史的影响。
清人入关承汉制,本着师汉制汉的目的,尊崇的仍是元明正统的朱学。在书法上,康熙雅好董其昌,乾隆专师赵孟頫,绘画推崇在明末逐渐确立的文人正统派绘画风格(即董其昌-四王画派)。这种虔诚的态度,固然对明末正统派画风起到了极大的推广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自明以来在士林中蔚然成风、个性解放的王阳明学的郁勃生机。
清宫收藏的审美观,在承正统派之外还促成了清代宫廷绘画的两大特色:其一是其崇尚的江南文人画趣味与追求富丽堂皇的宫廷趣味合而为一;其二是乾隆时来华的名家郞士宁所挟的西洋画风,在与前述江南文人山水与皇家趣味相结合的宫廷画风再度杂交,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新风。这两类画风,乃是“石渠”收藏“当代艺术”(即国朝书画)的主流。
此次故宫“石渠”大展,也可与上海龙美术馆正在举办的“盛清的世界——康雍乾宫廷艺术大展”相参看。这是上海私人藏家刘益谦发起的一次规模罕见的纯粹来自民间收藏界的清三代文物艺术大展,除了大量珍贵的工艺杂项,其书画皆清代宫廷画家作品,多“石渠宝笈”编著时代的“主题创作”,如《大阅图》《康熙南巡图》等,皆正牌“石渠”之国朝画,充分体现了清代宫廷绘画的特色与成就。
附带说明包括笔者在内的论者长期秉持的偏见,这种偏见缘于长期陶冶于追求清雅的江南画传统,更缘于江南画与富丽的宫廷趣味媾和产生的繁琐感。之所以称为偏见,是因为笔者近十年陆续见到清代宫廷画家的佳作,旧的观念逐渐改变。清代宫廷画确有繁琐之弊,但这并不足以掩盖当年的如意馆尤其是用色上的杰出成就。这一成就,事实上正是近代于非厂乃至张大千所擅“工笔重彩”的一大源头。“石渠”所藏国朝书画,其实正是学界尚缺乏深入研究的一座富矿。
稍加留心不难发现,“石渠”收藏的国朝画还存在一大空白。这一空白并非刻意而为,而正是崇尚正统的艺术观造就的副产物。
如前所述,明代崇尚个性解放、声势浩大的王学反映到书画创作领域,乃是由明末石涛、八大,或谓“四僧”包括新安派开启的扬州八怪写意画潮流,史称“野逸派”。
明眼人不难发现,这类画家的作品,在“石渠”收藏序列里是少得可怜甚至根本没有的。这并非乾隆帝的有意压制,而是因为那些江湖而非宫廷的“当代”画家,对于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而言,其实是不甚了解或者说是不屑了解的。他们非但名气不那么大,而且大多是个性古怪的歪瓜裂枣,有地方小吏,甚至还有从事过“颠覆国家”的反清活动,因而虽有地方商贾供养,但其名声完全不是从四王到钱维城、黄尊古、张宗苍等这些名门正派所能比拟。
然而,这股蛰伏民间二百余年的文艺力量,在与清宫所推崇的正统派审美拉开距离的同时,裹挟着清代考据学与碑学运动的成就,在封建王权逐渐瓦解的过程中,逐渐掀起了艺术变革的波澜。从与乾隆同时代的金冬心、郑板桥,到清末吴让之、赵之谦,再到民国时的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乃至张大千、傅抱石等,终于在近代画坛开启了在近代艺术史反动于四王正统派的另一股巨大洪流。在成为近代画史最为重要的流派的同时,上述画家发展完善了自唐至明一直暗流涌动的中国画大写意风格。并且这股潮流,在清代四王的“当代”画风独霸画坛三百年之后,在近代对封建意识的批判乃至除旧布新的过程中空前壮大,甚至于上一世纪末曾被艺评界解读为传统中国画几乎惟一的代表或者说是精华,余波至今不绝。这不得不说是拜盛清蔚为大观的“石渠”正统审美风靡所赐,引发或者说是反激出的另一大艺术史变迁的奇观。
- ChatGPT推出图片管理功能:AI创作更高效!
- 长安汽车新布局:今年推出20款新车,未来5年50款,全面发力新能源汽车市场
- 抢票关键时刻12306崩溃,网友呼唤客服解难
- 极石汽车创始人套现9亿后清空社交账号,反劝投资者耐心,引发深思
- OpenAI成立非营利委员会:揭秘四大顾问背后的新发展
- 抵御关税冲击,美国PC市场2025年Q1逆袭:出货量激增12.6%,库存量将大增
- 哈啰出行如何破解资金难题:借贷策略揭秘
- 全球电车风潮涌动:中国与欧洲领跑,同比增长29%的电动汽车销量新篇章
- 货拉拉五次冲击港股IPO:营收增长19%却估值跌回四年前,上市之路坎坷不前
- DeepSeek助力AI原生App:月活跃用户数翻番,开启智能新纪元
免责声明:本网站内容主要来自原创、合作伙伴供稿和第三方自媒体作者投稿,凡在本网站出现的信息,均仅供参考。本网站将尽力确保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及可靠性,但不保证有关资料的准确性及可靠性,读者在使用前请进一步核实,并对任何自主决定的行为负责。本网站对有关资料所引致的错误、不确或遗漏,概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本网站中的网页或链接内容可能涉嫌侵犯其知识产权或存在不实内容时,应及时向本网站提出书面权利通知或不实情况说明,并提供身份证明、权属证明及详细侵权或不实情况证明。本网站在收到上述法律文件后,将会依法尽快联系相关文章源头核实,沟通删除相关内容或断开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