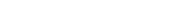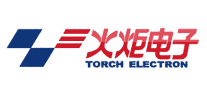在今年FIRST电影节上,青年导演张中臣站在领奖台上说,“如果不能用电影做表达,我会选择去死”,台下一陈欢呼。其实这符合很多时候外界对于电影行业从业者的想象,觉得他们充满着热爱、激情,以及“不自由,毋宁死”的洒脱。
但是,这并不是电影行业和电影人的全部,比如说2012年,还在北京大学读泰语专业的大一学生王玉超,被《人在囧途之泰囧》的12.7亿票房所震惊,“当时只觉得做电影好挣钱”。她没想到在9年后,会提笔写下自己电影剧本的第一行字。
自《泰囧》以后的几年,电影行业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来了各路资本,年轻人们也来到这里为爱发电、追逐梦想。
也是在那个浪潮之下,2015年,23岁的杨若芊从河南大学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毕业,为了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她又前往上海大学继续攻读电影学硕士。
每年都有很多像王玉超、杨若芊一样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地投身到这个行业里。
但这几年的电影行业,经历了资本泡沫、疫情重创,整体从业者的生存焦虑都在变得更重,即使是追梦的人也需要时常停下来充电,很少能再看见“不自由,毋宁死”那样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本职是导演的贝吉塔在家喝着Whisky熬夜写剧本、编剧王玉超暂时离开了北京、做影视宣传的郑小小经历了从降薪到失业全流程......
娱乐资本论(yulezibenlun)和包括制片、导演、编剧、宣传在内的8位年轻电影人聊了聊,发现他们其实和大多数打工人一样,在不断工作、开会、休假、重新投入工作、设立阶段性目标等。不过,影视行业作为有着足够可能性的行业,同时也给了不少人坚持下去的勇气。
疫情之后,作为电影人,也作为打工人,他们要如何在其中书写自己的故事线、以及如何共同为这个行业的未来探索一条道路,都是这次采访试图探讨的问题。
以及,当他们发现自己职业不仅和自身追求有关,更和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息息相关时,小娱也想试图探讨另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足够的财富,他们要怎么留下来?又会怎么思考自己的位置?
一个比较好的开始,等于一条更顺畅的前路吗?
27岁的贝吉塔毕业于重庆大学导演系,曾经在电影《半边天》以及待上映的两部院线电影里做执行导演。
“高考那年,我其实是陪朋友一起报名考试,结果他没考上我考上了。”贝吉塔就此进入了这个“家人并没有很支持,但自己却挺喜欢”的行业。
他的第一份剧组经验是在大三,当时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在贝吉塔的老家河南拍摄,他误打误撞进去做了两个月的场记。刚去的时候制片主任告诉他,实习生没钱拿,愿意的话先试一星期,能坚持就留下。没工资领对于贵在收获学习经验的贝吉塔来说没那么重要,所以贝吉塔刚开始很兴奋,“后来待了一星期就有点想回学校了,工作确实比较枯燥,接触不到创作”。但这两个月学习到的正规剧组流程,却实实在在地为他建立了一定的认知。“后来拍作业或者拍别的短片都会尽量用这套流程,把它制度化”。贝吉塔说。
也是因为这份经历,他和导演刘雨霖结下了缘分。那是贝吉塔无意间积累下的第一份社会资源,后来贝吉塔跟的比较大的电影项目几乎都和导演刘雨霖有关。这样的开头不自觉地让他跻身于行业里的潜力股。
比贝吉塔大两岁的杨若芊,也是科班出身,本科是戏文专业,硕士是电影学,正儿八经的专业对口、进入行业似乎水到渠成。但杨若芊大学就读的环境并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提供给她,因此她直到来上海读研二那年,才有了正式开始跟项目的经历。
最初,她跟着当时还是影评人的藤井树做新媒体、观影团,没有涉及到电影项目。“后来研二快结束的时候进了项目《荞麦疯长》”,当时还没到筹备期,杨若芊也不知道后来自己会承担一个制片的角色。“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感觉,没有经验,只能不懂就问,然后一点点总结”,后来这反而让她清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
不想做文字类工作、也不想离创作太远,于是《荞麦疯长》项目期基本结束后杨若芊来到了北京,成为了爱奇艺影业的执行制片。“当初考研的时候在上海和北京里选了上海,没想到最后还是来了北京”,杨若芊调侃。
她和贝吉塔相似,都是属于科班出身、入行时接触到了相对优越的资源,然后在今天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
在电影行业,资源和机会都很多,但能不能成,或能不能与你有关,一定程度上是靠运气。
王玉超是8位受访者中唯一因为念大学来到北京的人。此前的人生中她是外界的“学霸人设”,因此她没有参加高考,而是从家乡南京直接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的泰语专业。
“北大的高材生来做电影了?”这是她常常会听到的“调侃”。王玉超并不享受这些时刻,但在另一些时刻,她又不可避免的享受着名牌大学的资源。
“北大的氛围比较自由,每年都会办戏剧大赛”,于是大二那年她加入了学校的剧社,通过剧社的师兄间接认识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副教授杜庆春,开启了她电影道路的第一步。当然,这也是北京高校之间良好的互联沟通给王玉超带来的好处,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北京大学”这个活招牌。
杜庆春教授当时在大地文化做项目开发,需要一个没有经验的实习生,王玉超很顺利的去了那里。“我当时什么都不懂,去那儿之前,我每年进电影院的频率甚至不超过10次”,她也挺忐忑,“杜老师开会我就跟着开会,他说啥我就记啥,到后来才慢慢开始往策划进阶”。
大学毕业后,王玉超进入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读电影理论的研究生,之后又进入田羽生带领的新圣堂学习编剧写作。直到今年,她自己的长篇剧本也入围了FIRST的创投。这一切,都和当时被保送进名牌大学时的想象不一样。
名牌大学和优越资源的双重加持把王玉超引进了行,她成为了被看见的那一个。
但也存在一类人,可能不太需要靠运气。
陈多今年28岁,是西北某省地产大亨的儿子,目前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工作室,同时跟着某大师编剧写剧本,“明年很快应该就有个项目就要上了”。3年前他从家乡来到北京追求他的“电影梦”,“当时我什么也不会,虽然现在也还是在学习,但那会真的除了钱什么也没有”,听上去像是在凡尔赛,但陈多确实没有因为钱发愁过。当年来北京,父亲不同意,想把他留在身边培养,以后接管公司。“后来我爸没办法,给了我一张不限额的副卡让我来北京,怕我饿死”。陈多在北京干了一年多的编剧,积累了一些资源,但有署名的只有一部三线小网剧。“只能又回去拜托我爸,我现在这家工作室就是我爸投资的”,陈多的爸爸后来也托人搭了几条线,现在才有机会跟着某大师编剧写剧本。
和上述几个人都不同,陈多是依靠家庭资本,和自己的小有能力,挤到了行业里有可能被看到的位置。
没人能想得到,这些还算顺畅的、同时又指向不同方向的开始是不是好的开始,以及,后面这条关于梦想或是职业的道路,会更顺畅吗?
疫情没有压死骆驼,但让人思考:是职场还是梦想?还有资格选吗?
需要承认的是,对于一些年轻人而言,电影有时是一个巨大的造梦机器。但对于已经在电影行业有一些“工作年头”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想的更多是如何让自己的职业道路走得更远,尽力做一个有追求、有情怀的打工人。
贝吉塔一直想导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在重大毕业以后,贝吉塔去了上海,当时上海国际电影节对年轻导演也有创投类的相关扶持,他就带着自己的剧本去了,期间还得到了李霄峰导演的鼓励。“但我当时没太想明白,商业和自我表达都想要,最后本子也没过审”,虽然当时组委会打电话表示是因为题材原因,但贝吉塔心里清楚,很大原因是在于他没想好自己的方向。
在上海待了两个月,最后随着女友的离开,贝吉塔决定要北上。在北京,他一边写剧本、一边接一些散活儿,直到他再次遇见刘雨霖导演。“她让我别光写剧本,到时候把自己先饿死了”,自那以后贝吉塔开始经常性的和刘雨霖合作。
直到疫情发生,贝吉塔的工作被迫中止,他反倒开始有了大段的时间去写剧本。“当时买Whisky都买那种1.8升的,每天喝得醉醺醺地写到天亮”,其实他也焦虑,“之前拍的一些广告也因为疫情没有拿到尾款”,也不想问家里人张口,房租和其他开销就只能用花呗、借呗支撑着。
为什么不干点别的?贝吉塔不是没这么想过。有次他着急忙慌的赶高铁,北京的马路堵得水泄不通,贝吉塔只能坐地铁换乘。下班高峰人来人往,每个人都匆匆忙忙,他觉得很恍惚,“我在想如果我不坚持做电影的话,这会可能在家或者在哪儿酒也喝上了,什么也弄上了,会是另一种人生。”
后来贝吉塔又觉得,地铁上那些匆匆忙忙的人,“其实大家都一样,总得为了点啥坚持”。贝吉塔学的是导演,毕业后这些年也一直在电影行业磨练,不论是为了自身追求或职业考虑,离开的沉没成本太高,因此他暂时不想、也离不开这里。
“干这行的有一半是抑郁症,另一半是酒鬼”,贝吉塔说,“我是属于后者”。好在现在大多数项目都能陆续重启或开机了,只是疫情间歇性的反复会需要面临更换拍摄地的风险。对于贝吉塔而言,疫情那段时间来的快去的也快,现在只要能开工,他的剧本还能继续写,他就始终能保持着一个酒鬼的乐观。
和贝吉塔不同,王玉超在疫情当口的选择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研究生毕业之后她经朋友介绍去了田羽生导演所在的新圣堂,慢慢开始往编剧方向发展。“田导对我们很好,疫情的时候也没有在薪资或者其他方面亏待我们”,但王玉超却在疫情那会离开了新圣堂,不久后和留美回来的大学同学成立了工作室。
“部分原因是在于我的另一半在上海读博,疫情那会不方便来回跑”,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她想做自己的故事。但在那个时机“独立”,王玉超和她的合伙人都承担了更大的压力,“找活、接活、盘算公司账户余额”成了她近一年来的日常。除了为写自己的故事而努力,这更加像一次创业。
直到在工作室基本保持收支平衡之后,王玉超在今年元旦写下了剧本的第一行字,并且入围了前不久结束的FIRST创投。
后疫情时代,大大小小的电影创投并没有减少,但来到这里的资方却比以往谨慎许多。王玉超的剧本《三好生》在FIRST吸引了不少资方的注意,但大多都希望她可以修改得“走出一点自我、再商业一点”,王玉超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是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
但她依旧是幸运的,这个被她形容为“半自传”的故事还拥有能够被拍出来的机会。
相较而言,影视宣传郑小小面临的境况要糟糕得多,她几乎没有选择的权利。宣传作为影视行业靠近下游的岗位,当无片可上、无片可宣,资金链就面临着巨大风险。当时郑小小的薪资陆续从60%降到了50%,最后她所在的影视宣发公司在钉钉群里宣布了解散。
“当时有点泄气了,本来有可能在今年升职,但最后确实很无奈。”某重点大学制片专业毕业,从业两年多,郑小小没有积累下太多可用的资源,父母也无力支持她再干些什么,所以她没得选。
失业后的郑小小回到位于三线城市的老家,找了一份文案策划的工作,一直干到了现在。但对于影视行业,她依旧有向往,“如果是要选职业,我还是愿意尽量选一份更喜欢干的事,但应该不会再去北京了”,郑小小失败过一次了,她不愿意再来一次。
一位学编导出身后来转行商务的北电毕业生告诉小娱,在他的同学圈子里,“有钱或者有资源的还在北京,呆不下去的只能回家”,而离开北京的几乎就是离开行业了。对于郑小小这类人来说,疫情只是把这一时间节点提前了而已。
这场疫情打破了很多人的幻想,但也让更多人重新思考。对于这群年轻电影人来说,离不开或许是因为还有情怀、愿意做梦,但也因为一直学这行、干这行,亦没有想过职业上的第二选择。
像王玉超、贝吉塔一样的电影人,属于行业里的“中产”,经历过专业学习、拥有着不错的资源,离开的沉没成本太高,前路的希望又时隐时现,现阶段还是会选择留下。但更多的从业者是郑小小,没有更多可利用的资源,她们只能离开。
别的出路和设想
电影行业本身的难已经让许多人提前离场,疫情只是加速了行业人口的新陈代谢。直到如今,还剩下的这些人要如何继续留下来?
29岁的执行制片罗清,目前供职于某知名电影公司。2018年,她从待了三年半的公关行业离开,开始做电影。“其实当时没想太多,主要是为了帮朋友忙”,这一帮就帮到了现在。
“现在有点累了,觉得很多事情没意义”。
三年里,罗清差不多跟了三个电影项目,还有其他正在推进的、不能推进的项目不计其数。第二个项目快结束的时候,离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也已经过去了小半年,但她却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是这个行业的阶层问题对我造成了负面影响”,罗清告诉小娱,巨大的资源、财富差异造成了这里的阶层化,“不是光努力就能组个好盘、做个好电影的,疫情终将过去或被控制,但阶层问题不能。”
“比如你看喜剧只认开心麻花、业内大咖来来回回都围绕着那些人,都是一个道理”,电影行业内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当大把的财富、资源掌握在某些头部公司里,普通人很难干涉一部作品将由谁创造,以及最终如何诞生。
但年龄渐长、顾虑渐多,罗清很难再像三、四年前那样说走就走,她只能偶尔看看工作机会,另一边还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新项目里,“当年一起工作的同事基本都到了管理层甚至高层,我还要事无巨细的处理所有制片上的琐事”,罗清觉得挺魔幻的,但她也没设想自己什么时候会真的离开这个行业。
某种意义上来说,罗清也属于这个行业里的“中产”,但和贝吉塔、王玉超不同的是,罗清是转行而来,因此罗清对换行业的开放度比较高,因此如果在别的行业有好的机会,她也会考虑,“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而留下来的王玉超也有自己的焦虑。她很早就进入婚姻,但至今还没有把生孩子提上计划。“我其实不担心年龄大了但没有代表作之类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假设明年我的电影开机,那我一定没法生孩子。”
但谁也不知道哪个孩子会先来,王玉超现在做的最主要的还是两件事。一是继续修改自己的剧本《三好生》。从First创投回来之后,她和几个有意向的资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修改上也在做一些取舍,“希望可以在明年顺利开机”。另一方面,王玉超的工作室在最近也被纳入了一个大型的传媒公司,生存状况应该会比之前好很多,涉及的范围将会不止于电影,“因为如果我们坚持要做电影行业的话,首先得活下去”,王玉超说。
在今年10月份的乌镇戏剧节,还有一部根据王玉超长篇剧本改编的话剧即将开演。这些新势头都让王玉超充满了生命力,慢慢开始不止于一份事业或工作。
贝吉塔也终于给自己立了个Flag,通过创投或别的方式,“争取在30岁之前把第一部长篇给敲下来”。目前他手上的两个剧本都在稳步进行着,“身边人的反馈还算不错,都鼓励我继续写下去”,贝吉塔说。
随着这些行业“中产”喜忧掺半往前走时,开头提到的那类无需太多运气也可以进入此行的年轻电影人,他们则不太需要考虑生存,只要愿意干就可以永远在行业,也无需担心退路。
开头提到的陈多是,余小明也是。
去年7月份,大学毕业的余小明搭上了从纽约飞回香港的国际航班。在纽约大学帝势艺术学院,余小明拿的是电影研究和电影电视制作双学位。但因为疫情,他没能留在美国。
“在国内隔离期结束了就可以直接进片场,我觉得挺神奇的”,因此隔离期结束后,他直接去了爱奇艺的一个网络电影项目做特效导演。现在余小明在上海生活,拍短片、拍广告,同时为了丰富履历。目前,他正在准备一部自己的短片,“有一半的投资是来自于我父母”,余小明有点不好意思的回答,“我希望这个可以在我的履历上留下比较重要的一笔”。他渴望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无论是拍短片还是不久后可能再回美国读研,他还很大程度上拥有家庭资源拖底,这让余小明拥有着做梦的权利。
相似的还有呱呱,他入行三年,此前一直是剧集编剧。呱呱在今年退出了一个一线IP项目,“不想当这样‘被阉割的’编剧了,我觉得自己在被消耗,”他说。接下来呱呱转而开始准备自己的短片作品,未来可能去创投、参加电影节。“试试看”,交谈中他侃侃而谈,很有激情。
和陈多、余小明类似,“我不太担心生存”,呱呱说。对于他们几个来说,电影更多是梦想,不是养家糊口的工作,但能不能“出头”则是另外一码事。家庭资本把他们托到了这个位置,有点类似于行业资源和社会资源对贝吉塔、王玉超的作用。
后疫情时代,电影行业从一个难走到另一个难。而和陈多、余小明不一样成长背景的人才是大多数,他们在疫情之后的“生存焦虑明显比以前更严重了一些”,王玉超说,“所以大家也知道,干这行必须有点信念感”。
这种信念感,可能是依旧相信电影能造梦,也可能是愿意相信这份职业本身。阶层问题会长久存在,不担心生存只为追梦的人也会陆续涌入,对于更多的行业“中产”或者是没有资源的小白来说,“熬”依旧是唯一的出路。
电影行业本身不缺情怀,这些年轻电影人也不缺。当成一份工作,或许会“熬”得更快乐,但在贝吉塔看来,“要是真的不成,那就等到那天再说吧,可能我也不会怪谁。现在我只想做好眼前。”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来源:猎云网)
免责声明:本网站内容主要来自原创、合作伙伴供稿和第三方自媒体作者投稿,凡在本网站出现的信息,均仅供参考。本网站将尽力确保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及可靠性,但不保证有关资料的准确性及可靠性,读者在使用前请进一步核实,并对任何自主决定的行为负责。本网站对有关资料所引致的错误、不确或遗漏,概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本网站中的网页或链接内容可能涉嫌侵犯其知识产权或存在不实内容时,应及时向本网站提出书面权利通知或不实情况说明,并提供身份证明、权属证明及详细侵权或不实情况证明。本网站在收到上述法律文件后,将会依法尽快联系相关文章源头核实,沟通删除相关内容或断开相关链接。